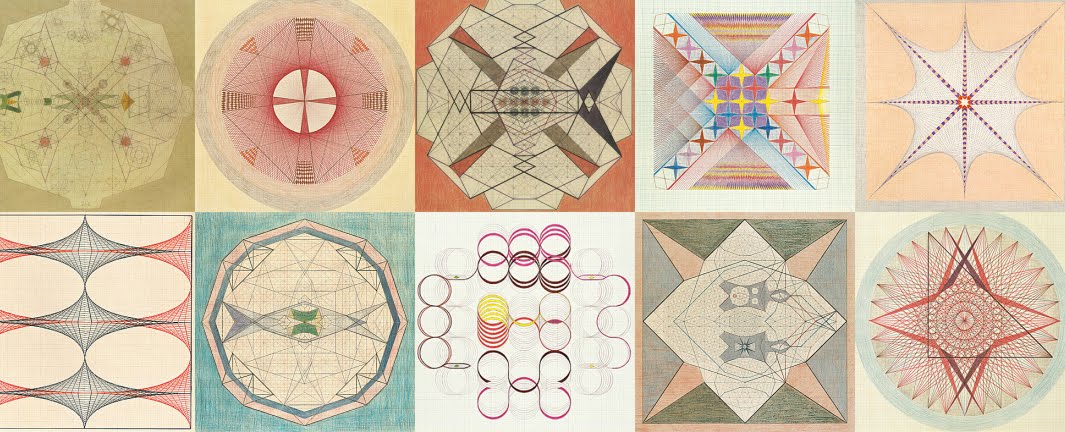您
六月十三日,天剛亮。
有一種預感,於是我輸入帳號,登入好一陣子以來都不太用的msn。
晃眼一過瀏覽了msn名單,獨獨一直看到「張老師」三個字。
稍早在小苗的暱稱上看到「張老師加油」,剪著片子的時候心理一直懸著
這件事。
拼拼湊湊著同學的、學弟妹離線的暱稱,然後,心一沉,真的是很重的一
沉。明明知道了卻又敲了一個仍在線上的學弟msn,親眼看到他打出
「張老師昨晚十一點時走了,於新竹醫院」
流不出淚,有那麼十分之一秒,我第一次感受到絕望這麼近。
那麼近的時候,身體來不及反應。
胸痛的毛病劇烈的在心口盤繞,好像突然鎖住了鼻咽鎖住了身體裡所有輸出
的管道。自家裡有著與張老師一樣的病痛的親人後,老是想起,
有一種預感,於是我輸入帳號,登入好一陣子以來都不太用的msn。
晃眼一過瀏覽了msn名單,獨獨一直看到「張老師」三個字。
稍早在小苗的暱稱上看到「張老師加油」,剪著片子的時候心理一直懸著
這件事。
拼拼湊湊著同學的、學弟妹離線的暱稱,然後,心一沉,真的是很重的一
沉。明明知道了卻又敲了一個仍在線上的學弟msn,親眼看到他打出
「張老師昨晚十一點時走了,於新竹醫院」
流不出淚,有那麼十分之一秒,我第一次感受到絕望這麼近。
那麼近的時候,身體來不及反應。
胸痛的毛病劇烈的在心口盤繞,好像突然鎖住了鼻咽鎖住了身體裡所有輸出
的管道。自家裡有著與張老師一樣的病痛的親人後,老是想起,
她不知道,這些日子以來我是如何把她看做一個強烈的希望,
這樣的希望也是在這個時候我才真正的意識到。
雖然和張老師相見的時間不多,
她那張柔和卻擁有強烈存在感的臉總是會在我心裡某一處紀錄著每一次的交
織。還沒見過她時,熟讀著她曾為作品寫的幾個簡單的字,憑著這單純的信
念進應藝所,進了應藝所,視線被越來越多的刺激左右,我不再是三年前的
自己。來越多的蒙蔽和累積、對好壞喜惡的界線越來越分明、對某些越來越
不耐煩、越來越多煩躁旁念。
但總是會在騎車的時候想起研一下期末時,張老師拿出的那盆蘭花。
張老師特別喜歡植物。安安靜靜的開出唯一的獨特的花,然後安安靜靜的結
果,安安靜靜的枯萎。安安靜靜的將生命掩入土壤延續於下一株生命。
那是最近一直縈繞在心裡的謎,生命的來來去去在這一年裡太多了、一次來
得太快了、太重了,幾乎無法負荷。
還來不及懷念就得被迫從容面對下一個離去。
然後才明白根本沒有真正的離開也沒有真正的釋懷。
時間無奈的輪轉將我身上的塵埃打了又打,卻掃了整個宇宙的情緒。
理不清的盼望、思念、恐懼、失望、冀望那些無以言喻的所有牽動都撲簌簌
的襲擊我鼻息。
我願意相信您是放手了把拳頭裡滿滿的美妙與幸福撒于我們,
也相信您不是離開而是化成空氣中聞得到的清香。
卻無法忍受某些說不出的甚麼侵蝕著我還想握有的一些明日。
-----
您曾用爽朗的笑聲對我短暫的談起我們同一天生日的事。並認真的告訴我,
來自母親血液的血型在這樣星座上是多麼令人羨慕的搭配,天生的樂觀者!
願我能循著與您放聲大笑的氣息,伴著往後我們一起的生日。
1960/12/19 - 2008/6/12
您曾用爽朗的笑聲對我短暫的談起我們同一天生日的事。並認真的告訴我,
來自母親血液的血型在這樣星座上是多麼令人羨慕的搭配,天生的樂觀者!
願我能循著與您放聲大笑的氣息,伴著往後我們一起的生日。
1960/12/19 - 2008/6/12